思考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了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相关规则。
1、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立法的特殊性
对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商标法中一般规定了三种计算方式:
1.权利人实施通常可获得利益;
2.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
3.合理的权利金。
从表述看,前述这些国家的立法提供的多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是可相互替代的,在实践中也不会产生必须依立法列举顺序适用的理解;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第71条,明文规定了可“择一计算”。
我国现行商标法的表述明显不同,其第63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无论根据文义解释还是立法机关的阐释,适用该条判定商标侵权赔偿额时,应“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依照本法规定(法定)”的顺序和方式确定;[1]即依次适用“实际损失”、“侵权所得”、“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方式。换言之,法定赔偿应当是最后的方式。
我国商标法为何在2013年修改时对63条采用按顺序适用的表述模式,立法机关并未说明,学界也未对此深究;笔者揣测,也许是为了在立法导向上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依序逐一尝试举证证明,以减少司法实践中不得已泛化法定赔偿带来的争议(后述)。
显然,第63条既揉和了通行的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所得两种计算方式,也引入了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和法定赔偿制度、同时采纳了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合理许可费计算方式,立法上看起来似乎很完美;但实际上,因其特别规定了损害赔偿额计算方式的适用顺序,笔者认为我国商标法的这一立法思路与实践经验相脱节,表现在:
其一,我国商标法在2013年修改之前,自1982年以来对商标侵权赔偿额采取的表述都是类似美国的“侵权所得”或“被侵权损失”的可选择计算方式,其间在2001年修改时增加了合理使用费倍数和法定赔偿两种方式;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法释〔2002〕32号第13条也对权利人可选择计算方法作了进一步阐明,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长期执行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可选择适用的政策。
其二,2013年商标法修改后在表述上明确了损害赔偿计算方式适用顺序,但其后并无相应的新司法解释出台对此作进一步说明,法释〔2002〕32号实际上仍在被各法院广泛适用,特别是其关于损失或利润以及合理费用的具体计算方式至今还被法院在判决中引述作为裁判依据。
长期的经验使得法院可能容易忽略在具体案件中应当依据现行法、并在判决中对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适用问题进行充分的说理,而2013年新增的惩罚性赔偿方式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法定赔偿的泛化适用和酌定赔偿的说理过简
如上所述,不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在实践中事实上均未严格按照现行商标法第6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顺序执行,不过,这一现状其实没有给最终的裁判结果带来实质性差别。根据诸多实证研究,无论是2013年商标法修改之前还是之后,权利人选择法定赔偿方式的均超过90%、有的高达98%以上。[2]
可见,即使依照现行法规定的顺序一一执行,按实际损失、侵权所得或许可费这几种计算方式绝大多数当事人都难以完成举证责任,因此索性都是把证据提交后直接请求或同意按法定赔偿计算;
另一方面,法院由于案件数量、时限等压力,没有精力按顺序一一要求当事人质证、而是乐于直接采用法定赔偿方式。
基于经验和惯性而缺少充分说理的法定赔偿方式之运用带来的不利后果是判决缺乏可预期性,特别是2019年修改的商标法将其上限提高到500万元(2001年是50万、2013年为300万),在表示强化商标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立法态度的同时,也引起各界对司法裁量幅度过大的更多担忧。
近些年来,我国司法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在判决中采用“酌定”解释判赔额的做法。例如,在老干妈案中,两级法院均认为原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所受损失或所获利润,也没法确定涉案商标的许可使用费,因此根据原告商标知名度、被告主观过错及经营情况、侵权情节等因素综合考虑并酌定判赔30万元。[3]
在拉菲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所受损失、被告侵权获益、商标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故结合原告商标知名度、被告明显主观恶意、侵权持续时间规模及销售状况、进口单价与销售价的差额等具体因素,同时考虑法定赔偿,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200万元。[4]在判决中采取这种“酌定”表述的并非少见。
用“酌定”表述赔偿计算方式尽管最贴近和反映司法实践,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法定赔偿”与其他几种计算方式、特别是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尽管法院在“酌定”时所考虑的因素和最终给出的赔偿额很慎重,但高度依赖法官自由心证、且过于简化的裁判说理方式容易给人带来“拍脑袋”的误解。[5]
笔者认为,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酌定”方法在我国法院广泛使用,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以及高效便捷性,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尺度,不利于发挥司法裁判的引导作用。
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近年来各地法院根据当地实践经验制定了一些指导性文件,对此作出了一些有益尝试,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颁布的《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第七章,对商标侵权的法定赔偿裁判标准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就全国性裁判标准的协调一致和司法预期稳定性的需求而言,有必要继续探讨以立法或更高层级的司法适用规则进一步明确几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适用关系,同时增强裁判文书相关部分的说理,尽量减少各界疑虑。
3
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相关法律规则的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在立法上解决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即改变现行商标法第63条的表述方式,明确所列举的多种计算方式是可选择方案、不再体现强制性的适用顺序,同时强调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院均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考虑并酌情判定赔偿额。当然,这需要按立法程序完成修法才能得以落实。
其次,需要在司法上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和规则,包括但不限于:
1、明确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性为原则
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侵权首先带来的是权利人利益的损失,损害赔偿尽管可有一定预防和惩罚的作用,但首要目的应当是填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尽管对实际损失进行举证、特别是证明损失与侵权行为因果关系具有高难度(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权利人不愿意披露自己的财务收支等秘密信息,这也是美国创设法定赔偿制度的原因),但当事人仍应当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首先对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尽力提供相关证据以供法院考虑,怠于举证而仅简单请求或同意按法定赔偿计算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判赔不利后果。
2、灵活运用举证妨碍制度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
商标法第63条规定了举证妨碍制度,这显然对权利人十分有利,但在适用时也须把握好尺度,对“尽力举证”作出恰当准确的理解。关于哪些证据被视为可接受的“尽力举证”材料、哪些属于法院判赔时的综合考量因素,前述北京高院的指导文件做出了一些指引,事实上各地法院也在总结并发布相关经验,这些举措需继续推进并由最高院协调一致有利于尽快形成共识。
3、明确按法定赔偿判定时法院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采用法定赔偿时,应当阐明当事人举证及认定情况,表明其已经尽力举证但法院无法确定具体的实际损失、必须根据其他因素酌定。
通常情况下,无法查清实际损失采用法定赔偿方式时,法院的考量其实已经包括了侵权人主观因素酌情加重责任,因此适用法定赔偿时也应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因素。[6]
台湾智慧财产法院曾判决非法销售海外代购6只假冒爱马仕包的被告按其正品最低单价500倍的法定赔偿标准赔偿,相当于一只包价值六千四百零六万元新台币(超过1500万人民币),在岛内引起轰动和反思。
4、明确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及其与法定赔偿的关系
我国商标法同时规定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实践中应明确惩罚性赔偿是建立在实际损失已确立的基础上,其适用要件是被告的主观恶意和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在侵权赔偿额已经根据原告损失、侵权人所得或合理使用费确定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倍数,其目的是为了体现对恶意侵权人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法定赔偿的适用中,法院在“酌定”时也会结合原告举证和被告的实际表现考虑主观恶意因素加重赔偿责任,但其前提仍是原被告关于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以及合理许可费的举证材料未得到法院采纳,具体数额是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的,其中也包含了有证据证明侵权人恶意这一惩罚性因素。
换言之,为区分制度功能,应明确惩罚性赔偿是实际损失、侵权所得或合理使用费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根据故意和情节的严重性增加倍数判赔,而法定赔偿则属于不必考虑也无法考虑具体数额倍数问题的一种综合判定。
惩罚性赔偿应当经原告请求而适用,原告须对被告明知自己侵权故意而为的恶意表现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情形通常由法院根据个案判定,典型的示例如原告已告知被告自己的合法权利并要求其停止侵权、被告仍继续使用注册商标制假售假直至原告提起诉讼。在实践中,故意的情形一般包括:
1.蓄意侵权,即明知他人权利存在且无正当理由相信自己行为不会构成侵权;
2.在诉讼中有故意隐瞒销毁证据等行为;
3.经营规模大或收入以侵权业务所得为主;
4.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
5.收到侵权警告函后未停止或采取补救措施;
6.存在故意隐瞒侵权行为的意图等。
我国商标法对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规定了侵权人的行政、刑事责任,在民事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还需要与此结合起来考虑。如果是“先行后民”或“先刑后民”已经处以了罚款或罚金,可能会使得惩罚性赔偿的执行落空。
另外,美国国会曾指出施以三倍的惩罚性赔偿对那些“将使其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朴实的小本经营者”不宜适用;实践中美国法院对个人破产、公司解散和面临财务危机无法雇佣律师进行抗辩的小微企业均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此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考虑侵权行为人生活状况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5、加强裁判文书对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及赔偿额判定的说理
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都是个永恒难解的问题,我们不能奢望法院的最终判决能做到真正的皆大欢喜。在商标领域,正品和仿冒品的市场价格有时候有天壤之别(例如地摊上售卖的假货与专柜中的奢侈品),根本无法证明原告所失、被告所得及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权利人最终选择法定赔偿的比例反而比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还要高。
基于实际损失证明责任几乎难以圆满完成的现实,惩罚性赔偿其实也很难适用,因此法院在判决中加强说理,阐明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标准、尤其是对各种酌定因素的考量和依据十分必要。
注释
▼
参见中国人大网“法律释义与问答”:http://www.npc.gov.cn/npc/c1853/flsyywd_lmlist.shtml。
例如,詹映:《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再调查与再思考——基于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的深度分析》,《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余秀宝:《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整体构建》,《法治研究》2018年第3期。
参见(2017)京民终28号、(2015)京知民初字第194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2015)沪知民初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
和育东:《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异化与回归》,《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
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与全面赔偿一样,是民事侵权责任判定中的一个原则,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 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5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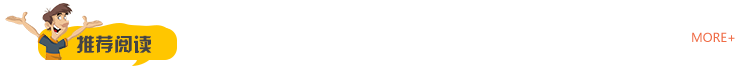
 防汛救灾 共建家园 励普教育全力驰援周口2021-07-27
防汛救灾 共建家园 励普教育全力驰援周口2021-07-27 河南卫视的出圈和他的商标 河南卫视一天注册265个商标2021-07-20
河南卫视的出圈和他的商标 河南卫视一天注册265个商标2021-07-20 今年上半年,南宁商标受理窗口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463件2021-07-20
今年上半年,南宁商标受理窗口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463件2021-07-20 2021年上半年长治市商标注册量较2020年底增加1749件2021-07-20
2021年上半年长治市商标注册量较2020年底增加1749件2021-07-20 商标被撤销 这些细节问题你一定要注意2020-10-29
商标被撤销 这些细节问题你一定要注意2020-10-29看的辛苦不如直接问!! 商标;专利;版权;法律